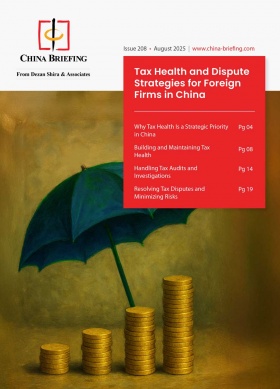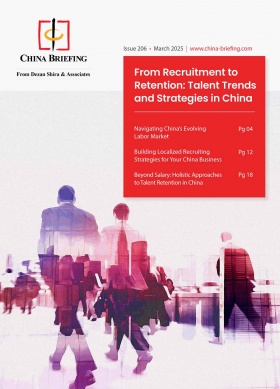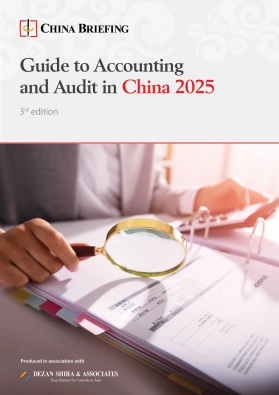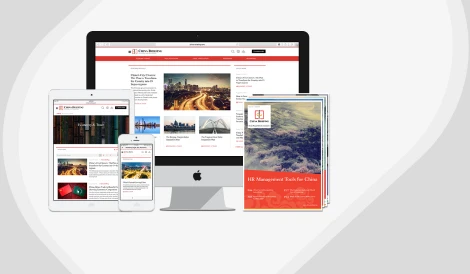美国对东南亚的关税政策如何影响中国的区域出口
美国总统特朗普正在积极推动东南亚国家达成相关协议,以遏制中国通过该地区进行商品转运的趋势。这些协议是为了提高中国商品仅经过简单加工后转口至美国的难度。然而,中国出口到东南亚的商品中,究竟有多少最终流入了美国市场?又有多少是真正满足该地区自身发展的需求?与此同时,关税及其他贸易壁垒可能对中国快速增长的东南亚出口带来怎样的影响?本文将探讨中国与东南亚日益紧密的贸易联系,并评估特朗普政府的关税策略对区域贸易格局的潜在影响。
在唐纳德·特朗普 2024 年的总统竞选期间,他提出了其标志性政策构想之一:对所有进入美国的商品征收 10%的全面关税,并对中国进口商品征收惩罚性 60%的关税。一如既往,特朗普再次将中国置于其保护主义议程的核心位置,他以美国巨大的贸易逆差为由,指责中国存在不公平做法,认为这些做法已使美国制造业空心化。
然而,自特朗普重返白宫以来,其贸易政策的激进程度甚至超出了许多人的预期。4 月 2 日,被戏称为“解放日”的这一天,特朗普政府宣布大幅提高关税,东南亚国家首当其冲。比如,越南和泰国分别被征收 46%和 36%的“对等”关税,这一税率甚至高于此前对中国征收的 34%的关税。此举令该地区许多国家感到意外,因为此前中美贸易紧张局势中,东南亚国家大多从中受益。
尽管特朗普随后将所有关税统一降至 10%,为期 90 天(后延长至 8 月 1 日),以便为双边谈判争取时间,但这些谈判的结构已使美国更广泛的策略愈发清晰。通过与越南等国达成贸易协议以及与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的潜在谈判,美国不仅寻求优惠的市场准入和降低进口关税,还嵌入能够限制中国通过第三国转运出口能力的条款。这些条款包括对转运征收更高的关税以及更严格的原产地规则,实际上这些措施都是为了限制中国的区域贸易。
在本文中,我们探讨特朗普的关税政策如何重塑中国区域出口格局。具体来说,我们将评估美国的保护主义(直接和间接)如何影响中国与东南亚经济体的贸易,又是如何影响该地区在全球供应链流程中的作用。
美国与东南亚国家的贸易协定谈判
7 月 2 日,特朗普宣布美国与越南已达成框架性贸易协定,越南成为首个与美国达成此类协议的东南亚国家。尽管最终协议的细节尚未公布,但特朗普表示,越南将被征收 20%的关税(低于 4 月初宣布的 46%的对等关税)。作为交换,美国将获得“全面进入”越南市场以及零关税待遇。不过,该协议还包括对转运货物征收 40%的关税。
这项贸易协议让我们大致了解了与其他国家达成协议时可能出现的条款。尽管越南得以就其直接对美出口商品争取到 20% 的关税税率,但协议中还规定了转口商品的关税税率为 40%,此举被普遍视为针对中国。
由于目前尚未公布有关该协议的更多细节,因此尚不清楚究竟哪些产品会受到关税影响以及如何受到影响,更不用说转运关税的原产地规则将如何定义了。不过,该声明确实清楚地表明了美国在与东南亚贸易方面的策略,并表明与该地区国家达成的进一步协议可能会包含损害中国的条款。
7 月 15 日,特朗普宣布美国已与印度尼西亚达成贸易协议,根据该协议,美国将把印尼进口商品的关税从 32%降至 19%,作为交换,印尼将对 99%的美国商品免征关税,取消对某些商品向美国出口的限制,并达成一系列商业协议。
目前 19%的关税在东南亚地区仅次于新加坡,按正常情况,这可能会使印尼成为转口贸易的枢纽。然而,印尼贸易部长表示,印度尼西亚将阻止转运以维护与美国的贸易协议。
|
美国对华与对东南亚国家互惠关税之比较 |
|
| 国家 | 美国互惠关税(2025年7月) |
| 中国 | 10% (2025年8月12日为止) ,此后 34% * |
| 新加坡 | 10% |
| 印度尼西亚 | 19% |
| 越南 | 20% |
| 菲律宾 | 19% |
| 马来西亚 | 25% |
| 泰国 | 36% |
| 柬埔寨 | 36–40% (预计) |
*中国商品还面临 20% 的“芬太尼关税”、301 条款下 25% 至 100% 的关税、232 条款下 25% 至 50% 的关税以及约 3.3% 的最惠国关税,总关税率最低约为 58.3%。
在 7 月 22 日美国和印度尼西亚发布的联合声明中,对于转口贸易的关税机制并未直接提及。不过声明指出,“美国和印度尼西亚将就便利原产地规则进行谈判,以确保协议带来的好处主要惠及美国和印度尼西亚”,这表明双方正在制定规则以防止转口贸易。
特朗普在宣布这项协议时称,从高关税国家经印尼转运至美国的货物,除了要缴纳印尼商品的关税外,还要按原产国目前的税率缴纳关税。这意味着从中国运往美国的任何货物都将同时面临中国目前约 52.5% 的关税税率以及印尼 19% 的关税。
联合声明中并未提及任何此类机制,但有可能在协议最终敲定之时会公布更多细节。由于该地区错综复杂的关税和贸易协定网络,这种机制的具体运作方式尚不明确,但这一迹象表明美国正在考虑针对中国出口产品采取多种策略,并堵住转口贸易的漏洞。
7 月 22 日,在菲律宾总统费迪南德·罗亚诺·马科斯二世访问之后,美国和菲律宾宣布已达成一项贸易协议,将菲律宾输美商品的关税降至 19%,仅比之前的 20% 稍微降低,作为交换,美国输菲商品将享受零关税。目前双方均未提及有关转运限制或关税的内容。
中国此前曾警告第三方国家不要与美国达成歧视中国出口商的协议。今年 4 月,中国商务部在一份声明中表示,中国“坚决反对任何以损害中国利益为代价达成的协议”。
越南作为中国商品的转运枢纽
由于缺乏透明的再出口数据、对供应链变化的了解有限以及难以区分真正的制造与转运或最低限度的加工,很难确定中国出口到越南的商品中有多少最终是运往美国的。除了转运之外,由于各种推拉因素,包括关税只是其中之一,该地区还出现了大量真正的制造业转移。
尽管如此,中国对东南亚某些国家出口的增长与这些国家对美国出口的增长之间存在密切关联,这强烈表明它们已成为中国出口商为规避美国对中国加征关税而进行转运的枢纽。
这在越南体现得尤为明显,该国对美出口在东南亚国家中增长最为显著,关键转折点是 2018 年美国和中国的贸易争端。2018 年至 2024 年期间,中国对越南出口的复合年增长率为 18.7%。同期,美国从越南的进口额复合年增长率为 15.7%。
过去 18 个月里,主要贸易产品的月度贸易数据也清晰地表明了这种关联。自 2024 年 1 月以来,中国对越南的电气机械和设备出口大幅增长,其中包括集成电路、太阳能电池板组件和计算机等产品。
2025 年 5 月,此类商品出口同比增长 53.5%,其中 2025 年 3 月的月度增幅最为显著,当月出口额较 2 月猛增 36%,而 2 月正是特朗普总统对中国商品加征 20%“芬太尼关税”的月份。
在此期间,美国从越南进口这些产品的增长幅度虽不那么显著,但仍引人注目。从 2025 年 2 月到 3 月,美国电气设备和机械的进口额猛增了 15.7%。2025 年 5 月,进口额达到 48 亿美元的峰值,同比增长 35%。
当然,目前尚不清楚在产品运往美国之前,越南究竟进行了多少加工和组装工作,又有多少只是进行了最低限度的加工。
中国对其他东南亚国家的出口
过去十年间,中国对其他东南亚国家的关键产品出口也有所增长,不过增速较慢。
过去十年间,泰国的发展轨迹与越南类似,中国对泰国的出口以及美国从泰国的进口同步增长,且自 2020 年以来增速显著加快。2018 年至 2024 年期间,中国对泰国的出口年均增长率约为 10.5%,而泰国对美国的出口在同一时期增长了 10.4%。
然而,总体贸易量仍要小得多。2024 年,美国从泰国的进口额仅为从越南进口额的 45%,而中国对泰国的出口额也仅为对越南出口额的 53%。
与越南和泰国不同,印度尼西亚和马来西亚从中国进口的商品与对美国出口的商品之间并未出现同样的镜像关系。过去十年间,中国对这两个国家的出口大幅增长,但对美国的出口增长速度较慢且更为不均衡,这表明中国对这两个国家的出口商品多用于其国内产业。
转运、回流以及东南亚市场的增长
尽管转运可能是中国对东南亚(尤其是越南)出口增长的因素之一,但它绝非唯一驱动因素。过去十年间,许多公司将生产从中国转移至该地区,尤其是进行最终组装和劳动密集型制造业,较低的生产成本是主要的吸引力。由于中国仍是众多行业所需中间产品的主导生产国,它正日益成为东南亚制造业中心的投入品供应商。这种区域供应链的转变极大地促进了中国对东南亚出口的增长。
2022 年《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的达成也为区域贸易带来了大量机遇,降低了其 15 个成员国(包括中国和主要东南亚经济体)之间的关税,并简化了贸易规则。通过减少贸易壁垒和优化海关程序,RCEP 让中国出口商能以更低成本和更高效率进入东南亚市场,进一步推动了区域贸易的增长。
最后,东南亚正逐渐成为一个独立的消费市场,一些经济体的中产阶级不断壮大,收入水平提高,对消费品、电子产品和汽车的需求也日益增加。这种结构性转变促使该地区从中国进口的商品增多,不仅包括工业零部件,还有制成品,这进一步表明中国对东南亚出口的激增反映了更广泛的经济融合。
美国关税和贸易壁垒对中国对东南亚出口的可能影响
经越南转运货物的关税
对中国出口影响最直接的将是美越贸易协议中达成的对经越南转运货物加征 40%关税的条款。鉴于中国对越南出口规模庞大,且其中许多货物极有可能再出口到美国,这对中国对越南出口的潜在影响是巨大的。
然而,尽管有明确意图阻止中国转口贸易,但转口关税在实际操作中如何实施尚不明确。确定货物的准确原产国本身就很复杂,尤其是在东南亚这种供应链深度融合的地区。区域贸易架构进一步加大了执行难度:在《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和升级版的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协定(CAFTA)等框架下,原产地规则旨在促进跨境生产网络,通常允许来自多个国家的部分成分获得优惠待遇。
这种复杂性使得区分真正的越南产品和那些只是途经越南并进行少量加工的产品尤为困难。例如,按照目前的《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规则,使用大量中国零部件在越南组装的成品可以合法声称原产于越南,因为该协定允许成员国之间有大量投入而不丧失优惠待遇。因此,对这类商品征收惩罚性的 40%关税将需要更严格且更具争议性的原产地规则,这需要海关部门之间有更高的透明度和协调性。
此外,越南和其他东南亚国家不太可能欢迎那些可能削弱其日益增长的出口产业或让遵守区域贸易协定变得复杂的措施。这种紧张局势表明,尽管美国可能会采取激进的关税政策来限制转运,但在行政管理和外交方面存在的实际障碍可能会限制这些政策的效果或延缓其实施。
太阳能产品关税
2025 年 4 月 25 日,美国商务部(DoC)宣布了针对从柬埔寨、马来西亚、泰国和越南进口的太阳能电池的反倾销(AD)和反补贴税(CVD)调查的最终裁决。该调查于 2024 年 5 月在拜登政府时期启动,认定在这些国家运营的中国太阳能公司既在美国市场倾销产品,又获得了中国政府的不公平补贴。关税税率差异很大:一些公司,如马来西亚的晶科能源,面临的综合关税约为 42%,而柬埔寨的一些公司面临的关税则超过 3400%。
这些发现表明,美国长期以来限制中国太阳能产品的努力仍在继续。2012 年首次征收的关税大幅减少了来自中国的直接出货量。作为回应,中国制造商将生产转移到东南亚,该地区很快成为主要的出口基地。到 2023 年,美国从柬埔寨、马来西亚、泰国和越南进口了价值 119 亿美元的太阳能电池,其中大部分是由与中国有关联的企业生产的。
如果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ITC)在 6 月确认美国商务部的调查结果,新的关税将实际上关闭这一出口渠道。这可能会对中国向东南亚出口太阳能相关产品产生重大影响,尤其是对硅片、电池片和多晶硅等中间投入品。随着东南亚组装商对中国太阳能组件的需求减少,中国向该地区出口的上游产品也可能下降。
更广泛地说,这一决定表明美国对涉及中国企业的间接贸易流动的审查力度加大。这给中国在东南亚的出口模式增加了压力,在那里,生产越来越面向美国市场。新的关税可能会扰乱现有的供应链,推高合规成本,并迫使中国太阳能制造商要么进一步实现本地化生产,要么探索其他市场。
钢铁和铝制品关税
2025 年 6 月 4 日,美国大幅升级贸易限制措施,将所有进口钢铁和铝制品的关税提高至 50%,这一税率是几个月前 2 月所征税率的两倍。尽管中国仍是这两种金属的全球最大生产国,但由于特朗普政府第一任期实施的长期 301 条款关税,中国对美国市场的直接出口受到限制。然而,新措施的更广泛影响可能会波及东南亚,因为中国材料在该地区面向美国出口的制造业供应链中发挥着关键作用。
中国对东南亚主要国家的钢铁制品出口情况表明了这种深度融合。从 2013 年到 2024 年,对印度尼西亚的出口额从约 14 亿美元增长至 37 亿美元;对马来西亚从 14 亿美元增长至超过 32 亿美元;对泰国从 9.6 亿美元增长至近 35 亿美元;对越南从 11 亿美元增长至 37 亿美元。这种持续增长凸显了东南亚对中国钢铁产品的依赖程度日益加深,尤其是在机械、电子和家用电器等制造业领域。
雪上加霜的是,美国商务部工业与安全局(BIS)于 6 月宣布,50%的关税也将适用于以钢铁为原材料的家用电器,比如冰箱、洗衣机、烘干机和洗碗机。这些电器如今在越南、泰国和马来西亚等国大量生产,所用钢材均来自中国。
尽管这些关税并未明确针对中国产钢材,但其结构却确保了中国出口商受到间接冲击。如果东南亚企业使用中国钢材制造销往美国的电器,那么仅钢材这一部分就要被征收 50%的关税,这削弱了将生产转移至中国以外地区的成本优势。
这对中国的出口影响重大。随着东南亚制造商在向美国市场供应产品时面临更高的成本和更紧的利润空间,对中国钢铁和铝材的需求可能会下降。随着时间的推移,关税可能会促使制造商完全减少受影响产品的钢铁含量,加快向替代材料或重新设计部件的转变,进一步降低对这些产品的需求。
从结构上看,这些关税有可能破坏东南亚融入以中国为中心的生产网络。尽管东南亚仍能提供低廉的劳动力成本和进入快速增长市场的渠道,但合规负担加重以及面临美国贸易惩罚的风险可能会促使企业重新评估采购、投资和设计策略。对中国而言,即便其对美国钢铁市场的直接敞口很小,但新关税的次级效应仍可能削弱其工业出口模式,因为这会削弱该地区对中国上游产业的需求。
遏制经印尼和马来西亚转运至美国的货物
美国正在积极与东南亚各国商谈双边贸易协定,而这些协议的一个核心特点似乎是包含针对中国货物转运的条款。
印度尼西亚和马来西亚等国已表示愿意收紧本国的贸易和海关制度,以争取与华盛顿达成有利的关税条件。
2025 年 5 月,马来西亚投资、贸易和工业部宣布,该国将成为所有运往美国货物的非优惠原产地证书(NPCO)的唯一签发机构,此举是为了集中并加强原产地文件的监管,与美国的贸易谈判做准备。与此同时,如上文所述,印度尼西亚已表示愿意限制中国商品的再出口,作为其与美国达成贸易协议努力的一部分。
尽管这些举措标志着态度上的重大转变,但对中国目前对东南亚出口的直接影响可能有限。与越南和泰国不同,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似乎并非中国货物转运至美国的主要枢纽。中国对这两个国家的出口,尽管规模可观,但更多地与国内基础设施建设和区域制造业相关,而非面向美国出口市场的最终组装。
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其更广泛的影响可能会更加显著。通过收紧原产地规则并提前贴合美国的执法重点,这些国家可能会降低自身作为未来中国企业试图规避高额美国关税时的再出口路线的吸引力。从这个意义上说,转运规则的收紧可能会限制中国调整其出口策略的灵活性,尤其是在那些曾考虑为应对贸易压力而将供应链转移至东南亚的行业。
与越南的情况一样,由于在区域贸易框架下确定原产国的复杂性,实施起来不会一帆风顺。
结局:加速回流,中国仍是关键的中间产品供应国
综合来看,全面的关税、转运限制以及与东南亚各国达成的双边贸易协议表明,限制中国通过第三国间接进入美国市场已成为特朗普贸易政策的核心要素。然而,这些措施更有可能加速贸易的地域重组,而非将中国从全球供应链中剔除,届时中国仍将作为中间产品的核心供应国牢牢嵌入其中。
由于美国加征关税促使最终组装环节转移,中国作为从关键矿产到电子元件等工业投入品的主要供应国的地位仍不可或缺。对于东南亚不断发展的制造业而言,这一点尤为明显,因为该地区在关键材料和产品的供应方面很难找到比中国更好的替代选择,这从中国对东南亚出口的大幅增长中可见一斑。
在这种情况下,完全脱钩不太可能。相反,全球生产体系正变得日益碎片化,中国供应关键零部件,而包括东南亚在内的其他地区则负责为美国市场组装最终产品。
- Previous Article Breaking Down the US-China Trade Tariffs: What’s in Effect Now?
- Next Article